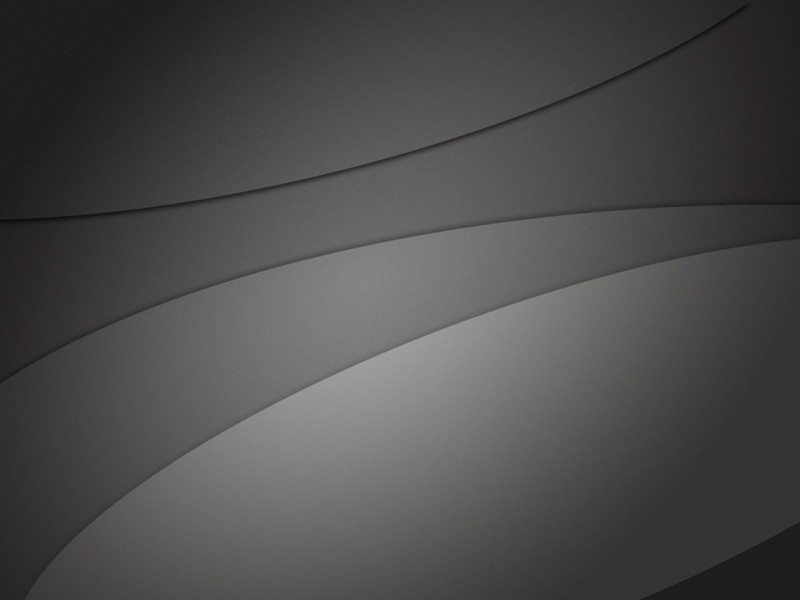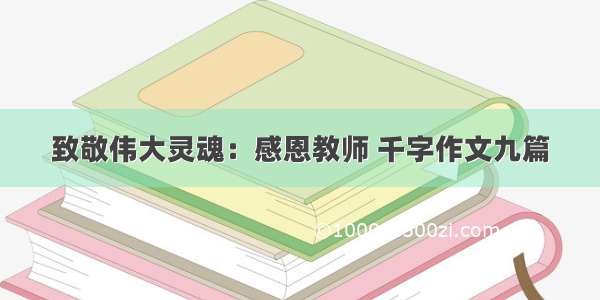她终其一生彻底拒绝了色彩,也从未描绘静物或者风景。“对于太阳与天空、太阳与海、太阳与大地之间那种乐此不疲的色彩游戏,她保持距离。”
自画像
走出中国美术馆,凯绥·珂勒惠支那些自画像的注视仍然相随。“她们”年轻或者年老,侧身向右或者向左。扭转头,回视你。无论以何种姿态,都沉默,如冰川掩在海面之下。
凯绥·珂勒惠支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从青年直到老妇,却唯见于版画和素描。在约束和限制之中,时间沉底于黑白两色。
“在这些自画像中,珂勒惠支不断地思索着自身,她在画中的姿态反映了这种自我思索;这些图画就像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自我陈述,只不过是沉默无声的陈述。以自画像的形式躬身自省并思索自身所处的时代,构成了珂勒惠支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部分。”
中国美术馆将正在进行的凯绥·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取名为“人:黑白的力量”,从某种程度,祛除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被赋予的单向度解读。展览从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凯绥·珂勒惠支博物馆、基尔市美术馆、荷尔斯泰因州立博物馆、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和一批私人收藏中选取了珂勒惠支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雕塑、版画、自画像、海报等各种形式。可以看到,母与子的关系,恐惧、绝望、死亡,这类母题如命运的复调,在她一生的创作中反复出现。
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名史作《德国人》里,将威廉二世到希特勒的那卷历史(1890~1940)直接取名为“衰落”。他并非指向国家经济——当时的德国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工业国家,柏林如同巴黎,已然是欧洲的文化融合之地——而是认为那个时期的德国人失却了精神性的荣光。路德维希写道,在威廉二世治下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快速向现代工业大国过渡,拥有数百万工人新阶层,工资远比其他国家为低,组织形式却更有效;同时由于好战的传统和严格的训练,服从性已经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虽然头上不再有18世纪普鲁士国王的棍棒,工人们却没有追求自由的向往。“那些在机床上生产炮弹,或者在微弱的灯光下一天10小时背驮煤块,用手推木轮车运输的人,仍然是那些当过三年兵,尝过各种拷打和惩罚滋味,而且从来也不反抗的人。”“德国工人最喜欢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重复地唱着:年轻人再也不回家/他们将战死疆场。”
珂勒惠支的一生,从1867年出生到1945年去世,就重叠在路德维希所形容的“衰落”德国之上。如果不了解她所处的时代,便难以真正接近她的艺术。“人”的生存境遇,人性中无休无止的挣扎是她作品里最恒久之物,而这些,远不是简单用“激进”或者“社会抗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覆盖。
凯绥·珂勒惠支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自16世纪,这座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就是新教根据地。许多支持宗教改革的德语和波兰语出版物都在这里印刷,开办于16世纪中期的哥尼斯堡大学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以传播新教而闻名。凯绥就在这样一个虔诚信奉新教的家庭里长大:她有一位深受教众尊敬的外祖父,曾在当地创立了德意志帝国(1871年建立)最早的“自由新教牧区”之一;而她父亲卡尔·施密特虽然出身泥瓦匠,后来也接任她外祖父的牧师教职,并以新教徒的勤勉积累财富,成了一个成功的建筑企业家。这些成长背景也许能够部分解释,凯绥本人以及她的艺术为何会终生保持一种严峻的清教徒气质:悲悯,煎熬,舍弃一切多余而直接抵达本质。
凯绥的父母生养了六个孩子,她排行老五。所幸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她从小显露的绘画天分没有被忽略,父母很早就将她送去跟随当地画家古斯塔夫·纳奥约克和铜版雕刻家鲁道夫·马奥勒尔学习。年岁渐长后,因为当时国立艺术学院还不收女性学生,凯绥先后进过柏林和慕尼黑的两所女子绘画学校,继续她的艺术课程。在柏林,大约是1881年左右,她结识了自然主义-现代派作家格哈德·豪普特曼和阿尔诺·霍尔茨,并深受其作品影响。后,格哈德·豪普特曼的戏剧作品《纺织工人》在柏林剧院上演,直接启发了她的《织工起义》系列(1893~1897)。这组作品由三幅石版画和三幅铜版画组成,珂勒惠支因此而在1898年的“柏林大艺术展”上成名。
前卫的传统主义者
如果说柏林求学时期的凯绥还在传统主义熏陶之下,那么到了几年之后的慕尼黑,反对德国官方艺术的“青年风格中心”以及“波希米亚一族的天堂”,凯绥开始追随“穿裙子的慕尼黑画家”路德维希·赫特里希(Ludwig Herterich),被反保守主义的自由氛围包围。
然而在婚姻方面,她仍是传统主义的。在柏林和慕尼黑的两段习画生涯之间,她与大自己4岁的医学博士卡尔·珂勒惠支订婚、结婚,成为凯绥·珂勒惠支。婚后他们从哥尼斯堡搬到柏林,开了诊所,生下两个儿子,一生相伴,连住处也没变过:怀森伯格街25号。1947年,在凯绥·珂勒惠支去世两年后,那里被改为珂勒惠支街56-A号。
1899年,珂勒惠支参加了“柏林分离派”的第一届展览,作品是两件蚀刻版画和一张素描。在19世纪末,德国的艺术状况十分芜杂:受到德皇威廉二世支持的风俗画和历史画占据主流地位,但效仿法国的前卫艺术运动也正陆续崛起,比如“分离派”和“青年风格”,就是官方艺术的激烈反对者。最早是1892年在慕尼黑,然后德累斯顿和柏林,叛逆的年轻艺术家相继建立“分离派”协会并开始在私人画廊组织国际展览,挪威的蒙克,巴黎的毕加索、马蒂斯等人都有作品送来参展。“柏林分离派”成立于1898年,第一届主席是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珂勒惠支从1901到19都是其会员,19开始甚至做过主席团成员。她和分离派在观念上的交集主要是蚀刻版画和素描。1881年她在柏林跟随瑞士籍画家、铜版画家和雕塑家卡尔·施道夫-伯恩学习时,后者就常常教导她临摹象征主义画家马克斯·克林格尔的版画。克林格尔认为绘画的任务在于将世界“按照它们应该的样子”表现出来,而素描的任务则与绘画相反,在于表现世界“不应该是的样子”,即那些“脆弱的、尖锐的、残酷的、糟糕的”事物。“生存的渴望与强烈的表现力”,克林格尔的作品风格深刻烙印在珂勒惠支一生的创作中。
1901和1904年,与身边那些年轻画家一样,珂勒惠支曾两次赴巴黎朝圣法国现代艺术潮流。第一次,她到访作为现代艺术推手的沃拉尔画廊,在那里见到了塞尚、高更和毕加索的作品。第二次她在巴黎停留数月,参加朱利安学院的雕塑课,还拜访了罗丹雕塑工作室。她后来的雕塑作品,从安放在哥尼斯堡大教堂的外祖父雕像到后期的《哀悼基督》,基本都停留在被她视为标杆的罗丹式的现代主义脉络之中。
与雕塑作品相比,珂勒惠支的版画——从蚀刻铜版、石版到后期的木刻显现了更前卫的语言。她有时会被人放在表现主义流派中谈论。德国的20世纪初期,对“表现主义”一词的表述其实在很多时候都含混不清。当19它最早出现在“柏林分离派”的展览前言里,是被用来指称布拉克、德朗甚至毕加索等法国艺术家的,之后几次出现也都如此,直到19一位叫保罗·费希特(Paul Fechter)的德国批评家,在第一部论述表现主义的专著中将这个词汇明确定义为“德国的反印象主义运动”,表现主义自此才和法国的立体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成为平行的流派。与德累斯顿的“桥社”艺术家路德维希·基希纳、施密特·劳特卢夫等人的作品比较,珂勒惠支和这些表现主义艺术家在观念上的相似性可能仅在于“坚定寻找表现主题本质的最直接的形式手段”。他们都偏爱版画和素描的那种黑白的力量,珂勒惠支尤其偏爱使用简单而风格化的线条来勾勒轮廓,“以一种感伤的诗性和言简意赅的表达姿态”。
但是,珂勒惠支在选择艺术语言的过程中显然更为单纯和坚定。她终其一生彻底拒绝了色彩,也从未描绘静物或者风景。“对于太阳与天空、太阳与海、太阳与大地之间那种乐此不疲的色彩游戏,她保持距离。”她的主题只有一个:人。
德方策展人、柏林自由大学文化与媒体教授克劳斯·西本哈尔甚至认为珂勒惠支是桥社流派的反对者。他说,在先锋派的艺术浪潮之中,凯绥·珂勒惠支可以说是一个特例,因为她并没有随着先锋潮流走,而是保留了自己对于艺术最纯粹的理念,“她可以说在这个浪潮中是一个传统主义者”。
死亡母题
在展厅入门的右侧墙面上,悬挂了一组珂勒惠支的女性肖像作品,《沉思的女人》、《女人头像》、《蓝色女工人的半身像》、《双手叠交的女人》……画中人的原型多为她的街坊邻居,其中不少还是她丈夫卡尔医生的病人。观看这个系列,目光最后总是停留在人物的双手上,或者,低垂的眼睛上。在艺术史上,这是非常罕见的一类女性形象,任何对于女性的形容词都显单薄而无能无力。
她着重描绘的是人对某些境遇的情感反应,而这些境遇并非由他自己造成,或者只在很小的程度上由他自己造成。女艺术家萨宾娜·莱普修斯评价说:“凯绥·珂勒惠支是少数几个成功地在艺术中实现了对人类这一受苦受难的造物的悲悯之心的人。”
珂勒惠支一家在柏林的住处位于普伦茨劳贝格区,属于劳工阶层聚居地。凯绥的画室就在丈夫卡尔的诊所隔壁,她常常在卡尔的诊所里发掘模特,目睹这些工人家庭的困苦现实,失业、酗酒,女人的忍受。在她这些版画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贫穷、社会不公正以及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珂勒惠支只是诚实记录事物本来的样子,并不想要传递什么理论观点。就像这些女性像,只是肖像。
“19前后,她仍是一个非政治艺术家,没有受到任何党派的影响。但是她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通过艺术来反映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生活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德方策展人克劳斯·西本哈尔的看法。
而在19,珂勒惠支曾有过一句纲领性的自我描述:“我同意,我的艺术是有目的的。”
她的“目的”,其实就是:人的处境。展览作品中有一幅19的石版画《父母》,画面上只有瑟缩在中央的两个半身老人:正面坐立的母亲和侧身坐立的父亲。画色极淡,省略,仿佛未完成,然而观看的目光不可控制地被人物两双交叠的手牵引,继而感受到强烈的痛苦正丝丝缕缕,从人物平静的身体姿态里传递出来。
1934年,珂勒惠支开始创作《死亡》。8幅石版画,用了三年时间。这也是珂勒惠支最后一组版画系列作品。其中的第八幅,看起来是她的自画像,一个老妇目光安详,正在平静地迎接死亡到来。死亡被描绘成一只手,看起来正温柔而慎重地触摸她的肩膀。“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珂勒惠支在日记中写道,“到如今这个年纪,我也许应该完成一组作品——关于(死亡)这个题目——它们应触及灵魂深处。就像老歌德说的:‘思考那迄今为止尚不可思考之物……’”
在她很多作品里,死亡既是安息,也是庇护和解脱。唯有在母与子的题材里,就像那幅寥寥几笔却无法忘记的《死亡擒住孩子》,死亡的面目要更复杂些。死神从身后袭来,母亲用身体捂住孩子,看向死神的目光低徊在惊惧、抵抗、挣扎和无助之间。
珂勒惠支作为母亲,经历了太多死亡。19,她在“一战”伊始就失去了17岁的小儿子彼得。1942年,她又在“二战”中失去了21岁的长孙彼得。1943年,珂勒惠支在轰炸声中给老朋友、作家格哈德·豪普特曼写信,告知自己和家人的近况。末尾,她说:“对,这就是我生活的轨迹,就如同老丰塔纳所写的那样:‘是啊,我还想要经历这些。’我还想要经历看看,这一切会如何发展,至少要尝尝其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