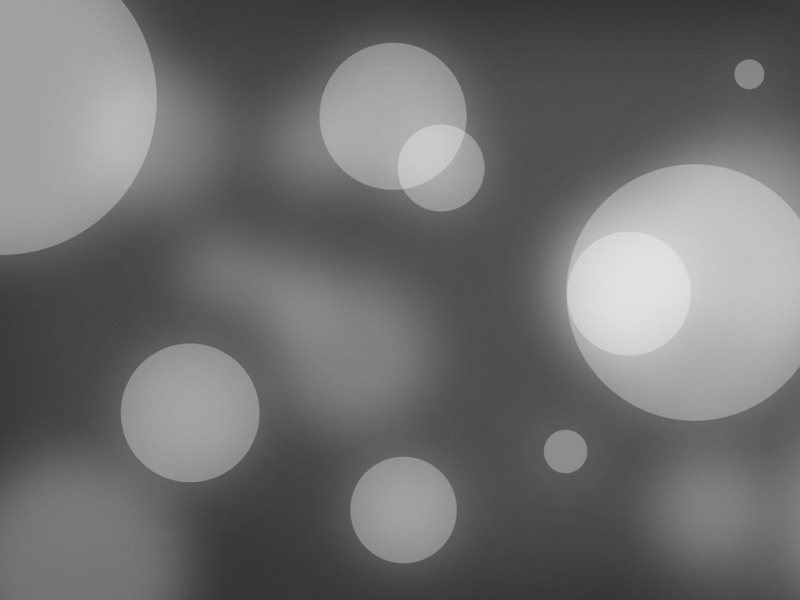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节选)
文学艺术问题并不单单是文学艺术领域内的问题。
这一判断并不难理解。但在中国,为达成这一识见,却在短短时间内驰过两个“急转弯”。起初,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学艺术从单一的“为政治服务”的机械框架中解放出来,人们运用文本学、叙事学乃至心理学的诸多理论做了许多颇有成效的努力,急切促成文学艺术“返回自身”;进人90年代后,人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才又发现当代的文学艺术早已经深深地陷人文化、政治、宗教、生态、种族、性别交织而成的迷惘之中,文艺学术与时代社会、自然之间已经累积了如此纷繁的难题。这时,文学艺术才又不得不“走出自身”,面对错综复杂的现代生活界。
或许,这“走出”与“返回”其实不过是文学艺术运动的常态,与基本粒子在原子内部的持续震荡相似,出走的同时也在回归,坠落的同时也在升腾,寂灭的同时也在显现,那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宇宙之舞”。在通常情况下,文学艺术的震荡周期要漫长得多,中国“新时期”的情况则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文学艺术无疑拥有其自身的属性、内涵,文学艺术注定又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自然的环境密切相关。也许,文学艺术只有在与其所处环境的折冲磨砺中,才能够显现出它自身的真谛。
……
“回归”的含义
现代社会中的情感危机、道德危机、个性危机、精神危机,最先并且最强烈地煎熬着诗人、艺术家的那颗敏感的心。然而,面对强大的社会现实,这又是一颗过于纤细柔弱的心。于是,诗人、艺术家们采取的抗争方式多半只能是“逃避”。当时代一日千里飞速向前发展时,他们却想逃往远古;当科学日新月异步步攀上尖端时,他们却想退回简朴;当城市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生活方式时,他们又倾心向往着乡村的牧草和田园。
卢梭
卢梭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他率先打出了“远离社会,回归自然”的旗帜,提出了“自然使人善良,社会使人邪恶;自然使人自由,社会使人奴役;自然使人幸福,社会使人痛苦”的主张。色彩斑斓的草地,清爽宜人的树林,碧波荡漾的湖水,繁星密布的夜空成了他躲避现实社会的世外桃源。
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则把文学的自然主义崇拜推向顶峰,在他看来,只有乡村生活才最有利于人类的本性与基本感情;天真的孩子、襁褓中的婴儿由于没有受过“庄严思想”的熏染,更多地葆有“神圣的灵性”,因此要比成年人、尊长者更容易领悟宇宙间“不朽的信息”,更接近自然中“真实的生命”。
那位内心孤独而又行迹匆匆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他短短的有生之涯几乎走遍了欧洲的所有国家,一心要找回自己的“故乡”。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心理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亲近或亲密”,是一个始终“被感情奉为神圣的地方”。日暮乡关何处是?最终被他寻到的竟然是伏尔加河岸边神秘笼罩的苍弯、宽阔浩荡的大川、耸人云霄的森林,以及林中那座古旧的木屋,木屋中那位银髯飘拂、目光炯炯、创作出《战争与和平》的老人。
在东方,崇尚自然、憎恶现代工业社会的则有印度诗哲泰戈尔。他愤激地指责:喷着浓烟的工厂,吞吐着金钱的贸易,以其秽物污染大地,以其喧嚣震聋人间,以其重压疲惫世界,以其贪婪撕裂苍生,这种“以效率的铰钉铆合在一起、架在野心车轮上的社会是维持不长的”。只有那幼稚的孩童、清纯的处女、涧上的新月、枝头的黄鹏、温馨的爱、诚挚的诗才是永恒的天国的福音。
在以上这些诗人的追求中,儿童、故乡、往古、东方、女性、自然、艺术、田园成了对抗现代工业社会、挽回世道人心的希望。他们的反抗是无力的,因为现代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反抗而稍稍放慢了自己的步伐;他们的反抗又是有力的,他们创作的那些优美的诗篇仍在代代流传,以其“深刻的人类直觉”洞察了人性的内在需求与工业机械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恢弘的弱效应,正如怀特海所肯定的:“伟大诗人的证言正好是在这种直接比较上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以往,我们的文学课程中总是把这些主张回归自然、逃离现实的诗人贬为“消极浪漫主义者”,甚至斥之为“反动”。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毫无觉察而又坚定不移地站在工业社会的立场上说话。时至今日,当地球的生态危机逼迫人们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已经有人在大声呼唤这种“反动”:“生病的地球,惟有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对经济优先进行革命,才有可能最后恢复健康。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必须再次倒转。”
勃兰兑斯
勃兰兑斯在论及英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时就曾指出:“自然主义转移到社会领域,就变得具有革命性了。”站在今日生态运动的立场上看,文学史上的这些“自然主义者”的历史价值,无疑应当重新评定了。诗歌之中的“回归”只是诗人的一种情绪和意象,承认这些“回归主义的文艺思潮”的历史价值是一回事;而真的要把“回归”作为现实社会问题探讨,那就需要弄明白“回归”的理论含义与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需要核查一下“来路”。
人类究竟在何时遇上了“岔道”,人类的选择究竟在何时出现了差错,以至酿成了现代文明的严重偏颇,说法不一。多数人是从启蒙运动算起,认为启蒙运动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一个有机完整的世界分割拆解了。还有人把责任追溯到文艺复兴,因为从那时起,理性的力量就已经被过度推崇,人类开始被抬举到万物之上、世界的中心。
也有人断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闹出了偏差:这两位希腊人的发现代表了人类的一个巨大而且必要的进步,但同时又是一种损失,因为原有的人类存在的完整性被分开了,从此,理性被看得越来越重,情性被看得越来越轻。正是这两个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制定了理念的法则与逻辑的法则,并把理念与逻辑高悬于存在之上,以所谓的“形而上学”开启了古代希腊的“童蒙”之心,开始了人类对自然以及对人类自身的算计、解析、简化控制。真正的启蒙应当说是从这里开始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开端,同时又是一个终结。他们开启的是一个条清理晰、井然有序的理性社会,终结的是一个“天、地、神、人”浑然和谐的诗意境界。这种说法似乎与中国古代的庄子在一则寓言中的判断是一致的,庄子也认为原初的那个“混沌”世界死于一个偶然的历史时刻,死于“倏忽”以善良的愿望对其混沌状态的开凿。那“开凿”当然也就是“启蒙”。
圣经
有人的推论还要早,认为在《圣经》“旧约”关于创世纪的传说中就已经确认了人对自然的管辖,因为上帝曾经对挪亚及其子孙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在自然界的所有生灵中,惟独人成了上帝特别高看的宠儿,这里就埋伏下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来路”已经如此漫长,那么,诗人们为自己的“回归”标定的“原点”究竟在哪里呢?
在西方,该是古代希腊。据说那时的人,精神与肉体还不曾分离,强壮的屁股与聪明的脑门一样庄严;神明与常人没有截然的界限,神、人可以相互交媾共同生儿育女;男人女人之间也不存在性别的社会歧异;那时的人生活简单,房子仅用来睡眠,衣服仅为了蔽体,三只橄榄,一棵洋葱,半个鱼头就足以打发午餐;那时的人生活又非常丰富,几乎三天两头过节,体育锻炼、艺术创作、宗教祭祀、游戏娱乐是密不可分的日常功课。
在东方的中国,这一“原点”该是古代哲人们描述的那个“至德之世”:人民“耕而食,织而衣”自给自足、自得其乐;“不尚贤,不使能,行无迹,事无传”无知无识,不图名利,不斗心眼;不但人与人之间如此和谐,而且大地上“禽兽成群,草木遂长”,人们“与禽兽居,与万物并”,“会而聚之,无以相异”,人与动物、植物、自然万物的关系也是那么和谐。
原点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已经难以考查清楚,上述诗人、哲人的描述也难免掺进个人的臆测,但在很早以前,人类社会确曾有过一段有机的、统一的、原生的、协调的、未经解析分化的历史,该是大体不差的,尤其在中国、印度和古代希腊。
那么,我们还能够返回这个原点吗?
岁月已逝,时过境迁,情随事移,现在的人群和土地已经不是老子、庄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人群和土地,现在的社会和自然也已经不是神农氏、伏羲氏、阿波罗、雅典娜时代的社会和自然,真要巴望在20世纪的今天捡回人类史前社会的那个原点,无异于刻舟求剑。
现在大约可以断定,诗人们潜心吟唱的“回归”,只是一种感伤的情绪,一种美好的憧憬,一些不无夸饰的言辞,虽说饱含着深刻的审美意义与批判意义,但毕竟只是一片虚渺的幻影。
如此说来,由于“回归”的不可能,现代社会的直线发展、高速发展、无限发展就取得了理论的、现实的合理性了吗?况且,更有人因此把所有“回归”论者统统说成是要让人们重新茹毛饮血的“复古倒退”者,在极尽嘲讽挖苦的同时,又竭力掩饰了现代社会的危机。
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现代社会中一些深人思索人类命运前途的智者,在探测“回归之路”时,已经为“回归”赋予了新的含义。
首先,“回归”决不等于机械的“倒退”,不是从来路上倒退回原点,这是显而易见的。海德格尔曾明确指出:当代人“不能退回到那个时期的未受伤害的乡村风貌,也不能退回到那个时期的有限的自然知识”,“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意见:我们这个行星的状况在不久或一般而言可以又变成乡村的田园风光。”
但是,“情况仍然会从根本上改观!”未来的社会应当“从人类的根源处萌发出新的世界”!这就是被哲学家赋予了新含义的“回归”。
“根源”即最初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那个有机统一的天地,这个天地虽然已经被现代社会搅得破裂颠倒,但神圣的原则依然在历史的飘渺处赫然高悬,“回归”即寻回这个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存在。
海德格尔
在海德格尔看来,“回归”完全与“倒退”无涉,而只是希望通过与古代希腊人、古代中国人的“对话”,为已经走进极致的现代工业社会寻获一个新的开端。“回归”实际上是端正人的生存态度,发掘人的生存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纠正人在天地间被错置的位置。“回归”是参照“原点”为现代重新提供一个行走的基础,“借着这个基础,我们能在技术世界内而又不受它损害地存在着”。这同时又是一场话语和观念上的革命,是一种精神上的改造运动,人类的精神生命有可能再次在此开花吐艳。
舍勒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整个西方文明是一个过分片面活跃的外向型过程,是一次以不合格的手段向前发展的尝试,“人类必须再一次把握那种伟大的、无形的、共同的、存在于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于永恒精神领域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以及这个第一推动力和世界进程的同契性。”在舍勒看来,“回归”,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一次自我“超越”,是向着人性丰富与崇高维度的艰难攀登。
文学艺术在这场事关地球命运、人类前途、历史进程的“回归运动”中,将如何呈现自
己,如何发挥作用呢?
在那个最初的原点,诗歌、艺术曾经就是存在与生存,就是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生长、繁息、创造、自娱、憧憬、祈盼,就是吹拂在天地神人之间的和风,就是灌注在自然万物之中的灵气。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使命”“最高存在”。人们曾经与诗歌、艺术一道成长发育,靠诗歌、艺术栖居于天地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或对峙于天地自然之外。如今,在个人与自然严重割裂对立的时代,艺术还有可能填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鸿沟、抚慰人和自然之间的创伤、开创新时代的和谐与均衡吗?
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个分裂的时代,艺术也早以蒙受重重伤害。现在需要的是高扬真正的艺术精神,凭着这种精神,艺术也许将会把我们重新带回涌动生长的大地,带向至高至上的神圣。
文学艺术在救治自身的同时将救治世界,在完善世界的同时将完善自身。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文艺学
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转换的关头,这决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
贝塔朗菲曾经如此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创的西方文明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周期已经结束。也还有人说,人类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真正的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当前,“第三次真正的革命”正向我们走来。关于这一“后工业”“后现代”的“新文明”的名称,人们还没有意见一致的看法,我们赞同这样一种提法: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
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恩斯特·海克尔
“生态学”(Ecology)在1869年刚由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时,只不过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一门研究“三叶草”“金龟子”“花斑鸿”“黄鼠狼”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动有趣则又无关宏旨的学问。进人20世纪后,生态学却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很快地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近年来,随着地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学更加引人注目,似乎已经成了本世纪末的一门“显学”。
在生态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所研究的课题还仅仅局限在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基本上采取的也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其结果是建立了诸如“昆虫生态学”、“草原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湿地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一些专门化的学科。正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生态学渐渐形成了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跨学科的研究原则。
到了本世纪初,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有人开始把生态学的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来,生态学开始渗入人类社会的种族、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促使了一批新的社会科学的诞生,如“城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生态学从此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人文色彩。
1962年,美国女作家瑞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作者一反常态地把满腔的同情倾泻给饱受工业技术摧残的生物界、自然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并以她生动的笔触将哲学思考、伦理评判、审美体验引向生态学视野。原本属于自然科学中一个小小分支的生态学,从此以后即延伸到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与我们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起来。保罗·布鲁克曾经这样评价卡森对于开创生态时代新文明的意义:“她将继续提醒我们,在现今过度组织化、过度机械化的时代,个人的动力与勇气仍然能发生效用;变化是可以制造的,不是借助战争或暴力性的革命,而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生态学已经确凿地展现出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乃至其他人文学科扩展的轨迹,生态学者的目光也渐渐由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扩展到人类的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层面上来,“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都已经成为目前生态学研究的一些新的生长点。所谓“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观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机体、精神的观点,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
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什么,文学艺术在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将发挥什么作用,文学艺术在当代的生态学家的心目中居于何等地位,在日益深人的生态学研究、生态运动的发展中文学艺术自身又将发生哪些变化,已成为一些十分重要而且非常有趣的问题。
怀特海
怀特海在论及19世纪英国文学时指出:正是这一时期的诗歌,证明了人类的审美直觉和科学的机械论之间的矛盾,审美价值是一种有机的整体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类似,“雪莱与华兹华斯都十分强调地证明,自然不可与审美价值分离”。自然与人的统一,更多地保留在真正的诗人和诗歌那里。这就是说,诗歌中表现出的艺术精神,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一个标志。
在海德格尔看来,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他把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社会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上:神话限制着科技的肆意扩张,歌唱命名着万物之母的大地,梵高画中的一双农妇的鞋子便能够轻易地沟通天、地、神、人之间的美妙关系。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是人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诗,“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只是一种表达的技巧,“人类此在其根基处就是‘诗意的’”。“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惟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他甚至宣称,只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那就是诗。
海德格尔的这些表述可能带有他自己的某些偏爱与夸饰,但从那时起,文学艺术的原则、审美的原则与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关系,倒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比如马尔库塞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物化”时就强调指出:艺术比哲学、宗教更贴近真实的人性与理想的生活,“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或起舞,来同物化做斗争”,惟有艺术才可能“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也曾经乐观地预言:“未来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
从近年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来看,被称作“环境文学”“环保艺术”“自然写作”的创作运动已渐渐汇成浪潮,一批优秀的生态文艺作品已蔚为大观,建立一门《生态文艺学》的尝试,已成为时代的呼唤。
“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不应仅限于“环保艺术”一类作品中,那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生态文艺”。而作为人类重要精神活动之一的文学艺术活动,从整体上必然和人类的全部生态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如此,因而都应当纳入生态文艺学的理论视野加以考察研究。一门完整的“生态文艺学”,应当面对人类全部的文学艺术活动,并对其做出生态学意义上的解释。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整理 | 张一川
编辑 | 李玉新